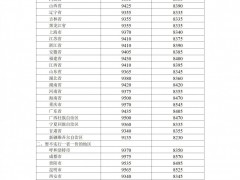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印发的《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再一次提出,“坚持以清洁低碳为发展目标”、“持续扩大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自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以来,中国明显加快了能源转型步伐,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按照中国中长期能源转型发展目标,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2050年,这一比重达到50%。但中国能源结构的现状决定了上述目标的实现必须大幅减少对煤炭的依赖程度。
《指导意见》提出,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计划总量不超过50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7.5%左右。
2020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亦是谋划“十四五”的关键之年。但与过往不同的是,今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遭受百年未遇的重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亦受到影响,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
全球经济亟待复苏,而推动绿色高质量复苏已成为全球共识。在后疫情背景下,未来五年,如何继续推进清洁低碳能源发展,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
煤炭依旧是最大挑战
作为《巴黎协定》承诺的一部分,中国计划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至65%。
事实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信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近期由能源基金会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举办的“能源中国——中国未来五年:为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增长注入清洁低碳能源”国是论坛上指出,中国为实现2030年履行《巴黎协定》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非化石能源占比、森林蓄积量等四个目标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尽管中国在碳排放上做出的努力得到全球广泛认可,但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正确对待和处理煤炭问题依旧是一项重大挑战。
由于能源资源禀赋和国际能源市场的限制,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和煤电仍会是主力军。截至2019年,煤电占比仍高达69%。控煤任务依然严峻。
我们看到,我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大力的同时,煤电装机总量实际上也在逐年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8.6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3.3%。其中,火电装机容量119055万千瓦,增长4.1%。这是五年来,煤电装机占比首次回升。
不仅如此,“国内低碳能源政策研究项目”6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除4600万千瓦在建煤电项目以外,中国至少还有4800万千瓦的煤电项目正处于推进阶段。
对此,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科技部原秘书长石定寰认为,“我们不能开倒车,‘十四五’不能走回头路,即使速度放慢,也要协调地推进能源革命”。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主任李俊峰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称,我国煤电目前处于“在纠结中发展”的局面。
“一方面,从环保角度出发,中国提出了增加电煤消费占比的要求,2019年电煤在全部煤炭消费中的占比已经从2015年的38%提升至48%。但另一方面,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到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比重高达40%,煤电碳排放的问题不容忽视。”
国家能源局《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力争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李俊峰认为,“煤电是托底的发电电源,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时,的确需要煤电顶上,但11亿千瓦的煤电装机规模上限,已经可以满足目前的发展要求。”
而对于既有煤电厂,则需要做高效、清洁化改造,减少煤炭使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祥琬表示,煤炭在发达国家主要作用是发电,而中国的煤炭消耗只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煤电厂做高效、洁净改造有客观的国家标准。从1980年的400多克,进步到了现在的平均308克,而先进的煤电厂只需270克。如果全国煤电厂都达到高效水平,煤电的耗煤就可以下降12%。
据统计,2018年,全球工业耗能占总耗能的29%,中国是65.7%;全球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例是30%,中国是59.2%;全球非化石能源占比为18.1%,中国是14.3%。由此来看,我国未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重在工业。煤化工、特别是因为氢能兴起而热度大增的煤制氢是非常值得的问题。
发展氢能,很多情况是从煤、水和气化而来。煤化工产生一公斤氢要诞生11公斤二氧化碳,油制氢要诞生7公斤二氧化碳,天然气制氢则诞生5.5公斤二氧化碳。
李毅中表示,目前我国氢燃料电池产业很热,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用化石能源制氢,所伴生的二氧化碳全部排放,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要大力加工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利用技术的攻关,实现产业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建议国家对煤化工、煤制氢等排放二氧化碳尽快制定标准规范,并且严格执行,从而使我国减排减碳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到2030年能够兑现承诺。
此外,散煤治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散煤是指电力和工业集中燃煤以外的散烧煤,包括小锅炉和小窑炉燃煤,以及居民生活和服务业分散使用的燃煤等,大多是未经洁净化处理直接进行燃烧的高硫劣质煤。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散煤用量较大,一年散煤的用量大概有7到8亿吨,占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近20%。散煤燃烧排放污染物约为电煤的10到20倍。以2015年为基准年,散煤燃烧对中国PM2.5浓度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在上述论坛上表示,如果不对散煤进行大规模清洁能源替代,到2030年散煤燃烧对中国PM2.5污染贡献将达到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的水平。
“中国未来要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一定是要走散煤从能源消费结构中退出的过程。”张强说。
事实上,2013年以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强力推进,散煤治理作为重要的民心和民生工程,被提上了日程。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散煤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如在京津冀地区,截止2018年底完成散煤治理1000万户,其中煤改气580万户左右,煤改电360万户左右,集中供热地热能等替代60万户左右。
2018年官方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央财政加大资金投入,5年累计安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528亿元。2018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下降42%,实现连续6年持续下降。
杜祥琬表示:“希望在“十四五”能提出基本完成以清洁取暖替代散烧煤。”未来,散煤治理需要在哪些方面不断加强?
张强表示,工业散煤的退出应该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明确落后行业和落后产能比较突出的地方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比如采取此类工业入园的方式,通过提供集中的热源,同时推进新技术研发和试点,把工业能源的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的推广结合起来,实现工业散煤的退出。
对于民用散煤,广大农村的居民负担不起清洁能源,选择用散煤、秸秆、木柴等,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还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甚至比室外空气污染还严重。未来在城镇化和农村奔小康的过程中,应该在消除贫困标准中,加入清洁能源使用这方面的指标。
可再生能源的时代机遇
新冠疫情为“十四五”开篇带来始料未及的新背景,造成的冲击会在‘十四五’初年形成市场疲软的短期局面,但这又提供了一个化危为机的机遇,可在这一形势下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和相应的改革。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因疫情影响的影响,带来能源的总供给超过能源的总需求的局面,也就是供需宽松的阶段。在能源处于供给需求紧张的状态时,为了应对需求的增长,很难有机会去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但在供需宽松的阶段,可以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等方式,化危为机,大力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和调整。
今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投资报告2020》预计,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能源投资在今年将可能下降五分之一,但疫情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最小。
例如,当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历史性跌为负值,国际煤炭同时大降,今年一季度,中国节能旗下太阳能和风电两家清洁能源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这既是由于近年来整个清洁能源的企业在经营管控和产业布局方面的优化,同时也体现了清洁能源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在区域公平、互联共享和普惠方面的优势。”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郑朝晖称。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杜祥琬认为,当前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每年能耗总量的增长大概是2%左右,这部分增长可以由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的增长来满足,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十四五”能源的增量主体就是非化石能源,进一步发展就会走向存量替代。高比例非化石能源会提供绿电、绿氢,提供低碳的供暖、供冷,使我们国家的能源更安全、更有韧性,并且以更经济的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令世界刮目相看。以风电和光伏为例,中国新增装机容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2019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为3010万千瓦;风电新增装机容量高达2890万千瓦,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48%。然而据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包括水、风、光、生物质、地热等等,开发量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十分之一,潜力巨大。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也出现大幅下降。2009-2019年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迅速,带动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下降80%左右,陆上风电成本下降近30%。
未来可再生能源的的“大有可为”,需要在哪些方面不断努力?
中国即将进入“十四五”时期,风电和太阳能行业也将完全进入平价上网时代。这对可再生能源的带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现有的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市场机制,并开辟新的方向和领域。
郑朝晖认为,技术创新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十四五”是风电等清洁能源走向主流能源的关键一步。新技术的应用,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以及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将加快行业从过去粗放式向经济化转变,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从而从根本上确立清洁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中美绿色基金会董事长徐林则建议,国家应当强化对风电、光电领域的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包括关键材料、储能技术、智能化技术等,藉此促进新技术突破,提高风能、光伏发电的转换率和储能技术、电池技术的水平。
徐林还表示,有必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现有的激励机制建立在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随着装机规模的扩大,这将导致政府补贴力度需要相应加大,这种激励方式不可持续。中国值得认真研究可行的制度,比如碳税制度。后者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同时可以通过征税抑制对化石能源的利用。
此外,李俊峰认为,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的重任落在风能太阳能身上,而真正制约风电光伏发展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市场以及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
“光伏和风电都需要大量土地,其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还要和生态文明建设划出的红线相适应、相协调,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做很多工作。”李俊峰说。
对于如何从机制上、制度上作出安排,李俊峰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层面应统一协调,将可再生能源布局与整个能源系统的构建和经济发展的大局相结合。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共同目标下,全面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关于李俊峰提到光电风电的安装空间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也表示,这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思路。
江亿认为,光电、风电都需要的是足够大的安装空间,但在西北等地大规模发展有许多附加成本。在城镇化、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城乡建设领域,建筑的屋顶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光伏资源。
中国城市建筑大概有50亿平米的房顶,有安装5亿千瓦光电发电潜力;在农村,农村房屋以及农业设施房顶面积达到200亿平米,大概具备20亿千瓦的光电发电潜力,一年能发电达到2万亿度。按照我们做的2050年中国能源发展规划,大概2050年有25到35亿千瓦的风电跟光电,一年出4万亿度电。按照这样的话,建筑房顶大概能提供其中的40%。
安装后还要解决发电用电平衡的问题,根据供给侧要求变化改变用电量。江亿认为,一方面,可以把智能充电桩跟建筑结合起来,用它来起到很大的柔性负载的作用,来接收外边的可再生电力;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就是在消费侧、用电侧,也可以起到灵活电源的作用、起到虚拟电厂的作用,可以把它当成灵活用电的负载。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自其它媒体的文章及图片,目的在于弘扬石化精神,传递更多石化信息,宣传国家石化产业政策,展示国家石化产业形象,参与国际石化产业舆论竞争,提高国际石化产业话语权,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在此我们谨向原作者和原媒体致以崇高敬意。如果您认为本站文章及图片侵犯了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