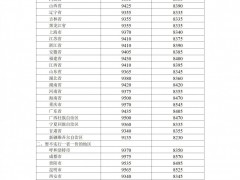“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发展煤化工,替代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以确保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和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发展煤化工面临水资源缺乏、装置综合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等制约。只有通过多联产技术,才能破解这些难题。”这是在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渭化集团董事长钱嘉斌提交议案的中心内容。
钱嘉斌指出,虽然不同机构对石油资源枯竭期的预测不尽相同,但2050年前后世界石油将达到峰值产量已经形成共识。即便算上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80年后,全球石油资源也将枯竭。从技术经济性看,煤炭是最现实可行的石油替代能源。尤其煤化工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的扩张,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能源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然而,发展煤化工又面临三大问题。
首先是水资源短缺。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煤炭等化石类资源与水资源呈逆向分布。而煤化工又是耗水大户,每生产1吨煤化工产品,往往要消耗10吨以上水。西部富煤省份正遭遇水资源短缺的巨大压力。
其次是能耗高。与石油、天然气化工相比,煤化工项目工艺路线长、设备多、投资大、投入产出比高,且需建设庞大的公用工程,导致煤化工装置综合能耗居高不下,比油气化工高30%以上。
再次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煤化工的核心就是生产合成气(CO+H2)或者氢气。由于煤炭分子中氢少碳多,要想经济地获得氢气,只有通过一氧化碳变换等方法实现。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钱嘉斌分析认为,前两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比如水资源短缺问题,可以通过水权置换、南水北调、蓄水补水工程,或者采用先进空冷、凝结水回收、废水处理与中水回用等技术加以缓解;能耗高的问题,也可通过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能效审查等办法加以遏制。唯独排碳问题,不仅难以解决,而且刻不容缓。
说其难解决,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捕集与利用不仅成本高,而且一些关键技术尚未突破。目前被广泛使用的深埋和注井采油技术,前者存在着很大风险,后者二氧化碳并未转化成其他产品,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资源化利用。至于二氧化碳生产碳酸二甲酯、降解塑料、气肥、碳酸饮料等,由于规模小,对二氧化碳的消耗十分有限。
说其刻不容缓,是因为从今年1月1日起,欧盟航空碳税法案开始实施。表面上看,这一法案似乎与煤化工没有瓜葛,事实则不然。因为欧盟航空碳税法案的实施,等于颠覆了《京都议定书》的原则与柜架,要求发展中国家履行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排碳义务。假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效仿欧盟的做法,甚至扩大到地面交通、海上交通及其他更广泛领域,那么,《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将不复存在,我国碳减排压力将陡然增大。
为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我国政府将严格控制火电、 钢铁、焦炭、水泥、建材以及煤化工等高耗能、高排碳行业的规模和速度。与电力、钢铁等行业相比,目前煤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地位和作用要小得多。一旦遭遇政策打压,煤化工产业无疑会首当其冲。从这个层面讲,排碳问题已经不是普通的环保问题,而是决定中国煤化工产业成与败、生与死的关键。“摆脱困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多联产。”钱嘉斌说。
其理由有三点:第一,多联产能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降低单位产值能耗;第二,多联产能通过水、热、气、电、功的梯级利用或重复利用,大幅降低装置综合能耗和水耗;第三,多联产可以借助不同技术与工艺路线的耦合,实现优势互补,减少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
比如,通过IGCC多联产技术,实现煤基发电与煤化工联产,装置能源利用效率可较单一发电或煤化工提高30%~50%;将焦炭—冶金—化工装置集约耦合,不仅能实现余热余压的全部回收利用,还能使炼焦过程副产的焦炉煤气生成合成氨、甲醇等化工产品。并将苯、萘等副产品通过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消灭排碳问题。
又比如,醇、碱、氨联合工艺,可利用氨合成过程中的一氧化碳生产甲醇,富余的二氧化碳生产纯碱,甲醇合成后富余的氢气生产合成氨。通过这样的上下游联供,可大幅减少二化碳排放。以一个30万吨煤制甲醇、30万吨煤制合成氨和30万吨纯碱为例,采用上述多联产工艺后,年减排二氧化碳达70余万吨。
再比如,一期总投资232.5亿元的延长—中煤靖边煤气油综合利用项目,由于将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石油化工对接耦合,实现了碳氢互补与平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439万吨。在不增加任何原料投入的情况下,新增产甲醇15万~27万吨,节约标煤41.9万吨,节约新鲜水1000余万立方米,资源利用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